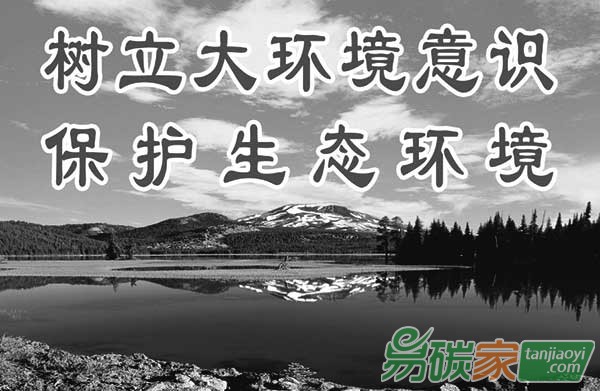燃煤電站這個用煤“大戶”已經被公認為引發霧霾的“元兇”,污染物治理成為了治霾的關鍵,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也成為霧霾頻發之下公眾最關注的話題。在此背景下,“近零排放”的概念應運而生,而其所帶動的千億級的環保
市場究竟會給我國大氣環境乃至經濟和民生帶來怎樣的影響仍然難以預料。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
北京國能中電節能環保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國能中電”)董事長、國家環保部燃煤大氣污染控制工程技術中心副主任白云峰先生。
中國能源報:您怎么看待目前“煤改氣”、“去煤炭化”等熱議話題?
白云峰:從2011年開始,關于中國煤炭高效清潔利用的話題就沒停息過,有人提出通過“煤改氣”等手段實現“去煤炭化”,以期通過減少燃煤總量降低燃煤污染物排放。這種觀點并不可取,我們認為,應通過節能
減排的技術手段降低單位GDP的能耗進行“控煤”,而不該是“去煤炭化”。面對自身一次能源結構的現實,靠“去煤炭化”解決污染物排放的
問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其次,國家能源戰略是事關社會發展的安全問題,通過能源進口等辦法試圖調整能源結構是不現實的。據我了解,我國工業能耗占全國能耗的百分之八十,所以,控制工業能耗是控制煤炭消耗的重點。其實燃煤并不是“洪水猛獸”,我們可通過相應的節能改造,設備、技術的更新升級及提高煤炭利用的集中度提高燃煤使用效率。同時利用最先進污染物治理技術使得燃煤污染物排放達到燃氣的水平,也就是“近零排放”。
中國能源報:您認為我國燃煤污染物排放治理技術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白云峰:中國大氣污染治理的核心在于提高煤炭使用效率,合理降低煤炭消耗量,并對燃煤排放的污染物進行大力治理來降低燃煤大氣污染排放總量。目前國內的污染物治理技術手段已經完全能使得燃煤電站達到 “近零排放”標準,但是如何滿足國家環保強制要求,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近零排放”及燃煤企業的自身需求,需要環保企業為之出謀劃策。作為環保企業要加大研發的投入,從技術上不斷創新、不斷突破,使得“近零排放”能適應我國復雜多變的燃煤情況及波動較大的鍋爐負荷。同時各類污染物治理設施應當系統、協同、高效、可靠設計,以降低環保設施的基建投入。同時要實現環保設施低能耗,低成本運營,盡可能減少環保系統能耗。
目前燃煤電站污染物“近零排放”治理的認識上出現了一個誤區,“唯指標論”,認為“近零排放”即是對燃煤污染物進行改造,使得SO2、NOx、粉塵達到“近零”要求以簡化環保系統配置。其實達到了目前國家強制要求的指標并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近零排放”,造成霧霾還有些很關鍵的污染物,比如重金屬、酸性氣溶膠、PM2.5等,這些就需要在電站污染物處理設施的末端采用“濕式電除塵”技術,確保粉塵排放的同時減少上述污染物的排放。
中國能源報:許多業內專家認為《行動計劃》要求的排放標準過于苛刻,按照此排放標準進行環保設施改造十分不經濟。對此您如何看待?
白云峰:關于國家《行動計劃》,發改委、國家環保部、國家能源局是經過多方面調研和科學論證得出的,那些所謂的排放要求過于苛刻的論調其實是不懂技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目前國內經濟發展已經受到了來自資源和環境的約束,政府有關部門極力主張以燃氣的排放作為標準,提出了燃煤發電機組大氣污染物“近零排放”的新標桿,這是大勢所趨,也讓我們看到了政府治霾的決心。
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的電廠都已經加入了“近零排放”改造的大軍,我認為這是發電企業社會責任感的體現,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成功的案例充分說明了“近零排放”的技術已經完全能滿足現實需要,“近零排放”技術已經日趨成熟,這是符合我國
電力行業的實際情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標準的提升固然會引發顧慮,但這些困難我們通過技術創新都一一克服了。例如,國能中電實施了上海外高橋百萬機組的脫硫改造,在全國率先達到了“近零排放”的標準,目前已經穩定運行一年多,這就是最好的實踐證明。
有人認為企業“近零改造”資金投入過大,我覺得需要特別闡明一下,所謂的改造,是在原有系統及設施的基礎上進行升級改造,而不是顛覆性的創造,不是推倒重建。我們在強調“近零排放”的同時,還通過提高環保裝置的節能效果,為電廠降低環保裝置的運營成本,讓環保不再成為企業的經濟負擔。
原標題:近零排放技術趨于成熟——訪國能中電節能環保董事長白云峰